■我母亲生前唯一的照片。
作者:杨明伟
那个年代,对于我母亲来说,照一次相,洗一张照片,还是一桩“非常难得的事”。她生前只照过一次相,也只洗了一张照片,那是在1981年的春末时节。
那时,我十多岁,记得村里人要照相的话需走路过去圩镇照相馆,照了之后一般要七天才能冲洗出来。偶尔有个别师傅为招徕生意,挎上相机包,到乡下吆喝着照相。
一天上午10时许,村里来了一位武冈县城照相馆的师傅。县城来的照相师傅技术当然好。我母亲知道后很高兴,因为她觉得有了孙子,三代同堂应留个纪念。于是,她绾着发髻,穿着整洁的衣服,梳妆打扮了一番,高兴地抱着四五个月大的孙子,在厨房门前一棵开着雪白花儿的梨树下,微微笑地对着镜头,让师傅“咔嚓、咔嚓”地照了几下,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照相。为了不多花钱,母亲只洗了一张2寸大小的黑白照。
1984年我国开始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。1988年的秋天,国家全面铺开,当时,乡政府派出所派人到各个村寨负责村民照身份证的相片,村民交四毛钱照相费可洗五张黑白照。但年龄过了55岁的村民,是不要求办居民身份证的。所以那次照身份证相片,56岁的母亲没有弄。
再后来,母亲年岁渐渐增大,身体每况愈下,家里收入也不怎样,开始是因为我读书要钱,后来考虑我没成家,要帮我存点结婚的钱。所以,一分一厘,母亲总是掰着指头算着用的。直到64岁的她于1996年9月得了胃癌去世,都没有照过第二次相。
其实,母亲是很想照相的,她曾在我身边喃语过“很想照几张照片寄回黎平娘家,让娘家人看看……”
其实,我很明白母亲的心思,她很想邮寄几张照片给娘家人看看,想表达惦记亲人之情,以此感激几个“舅舅”对她的养育之恩。
母亲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,是个孤女,吃“百家饭”,靠几个堂哥养大。解放前夕,父亲从城步苗乡到贵州黎平做点小生意,在那里父亲和母亲结了婚。几年后,母亲于1958年随父亲用肩挑着家当,携带两个小孩(小的后来夭折),步行崎岖山路数月,回到杨田村安家。我家穷得叮当响,很多人瞧不起,从贵州远嫁到苗乡的母亲,却和我父亲“白手起家”,硬是“撑起”村寨里第三座砖房子,十里八村,刮目相看!
母亲回到湖南生活的近40年,因交通不便,又忙于一年四季的农活、家务活等,当然,更重要的还是没有路费,所以,母亲回娘家“探亲”也就屈指可数的3次。
母亲去世后,为了家人永不忘却,我将母亲抱着我侄儿的那张黑白照,拿到照相馆,让师傅技术处理,遮掉我侄儿的影像,翻拍放大,然后拿给专业碳相的罗师傅,根据翻拍的照片画出母亲的遗像。这样,三兄弟家里都能有母亲的遗像安放。
“南北山头多墓田,清明祭扫各纷然”。序春草绿,今又清明。今年疫情阴霾依然笼罩人间,而远在异乡的我,无法到母亲的坟墓上烧香祭拜,只能在家里母亲的那张遗像旁叩叩头。睹物思人,一看到母亲生前那张唯一的黑白的照片,总能让我触景生情,想起她那沧桑而又自强的岁月,想起她那勤劳而又俭朴的人生,想起她那对我“做人如感不起恩但至少要懂得知恩”的教诲……
■统筹:陈红艳 麦婉诗
标签:
-
1科技手段助力公益诉讼 大大提高了办案的效率和精准度
-
2高通宣布新一轮100亿美元股票回购计划 没有设定截止日期
-
3浙江富阳大源镇举办“婆媳同心”主题笔会雅集活动
-
4摩迅科技:“VR云看展”是如何为展会数字化赋能的?
-
5我爱我家志愿者服务队:弘扬抗疫精神 守护社区平安
-
6万亿睡眠市场正在觉醒,福气多智能床展现高端科技
-
7CCBEC 深圳跨境展开启更多线上平台新功能 踏上云之路
-
8联想集团终止科创板IPO 柳传志约1亿元高薪酬传闻四起
-
9技术领先,出行0焦虑,瑞虎7 PLUS新能源闪耀瑶光2025 奇瑞科技DAY
-
10全新换代 全新设计!全新一代瑞虎7 PLUS内饰曝光 科技感、豪华感爆棚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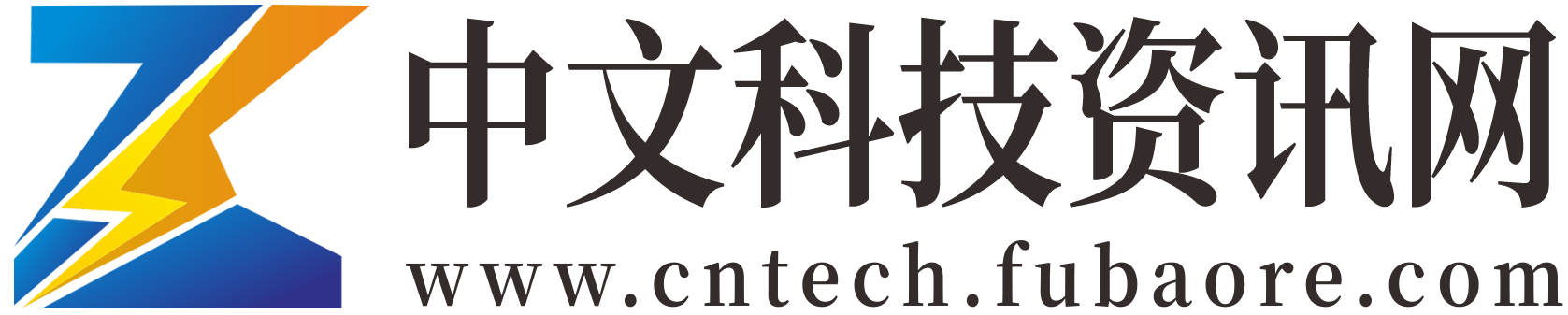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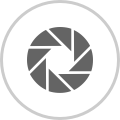








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
营业执照公示信息